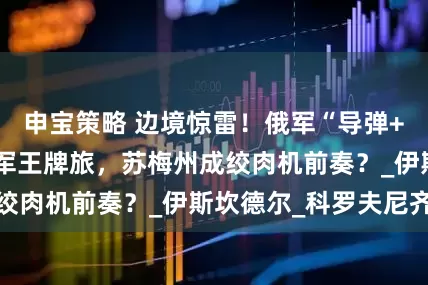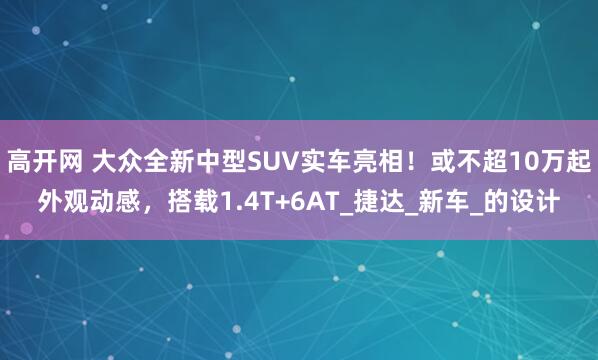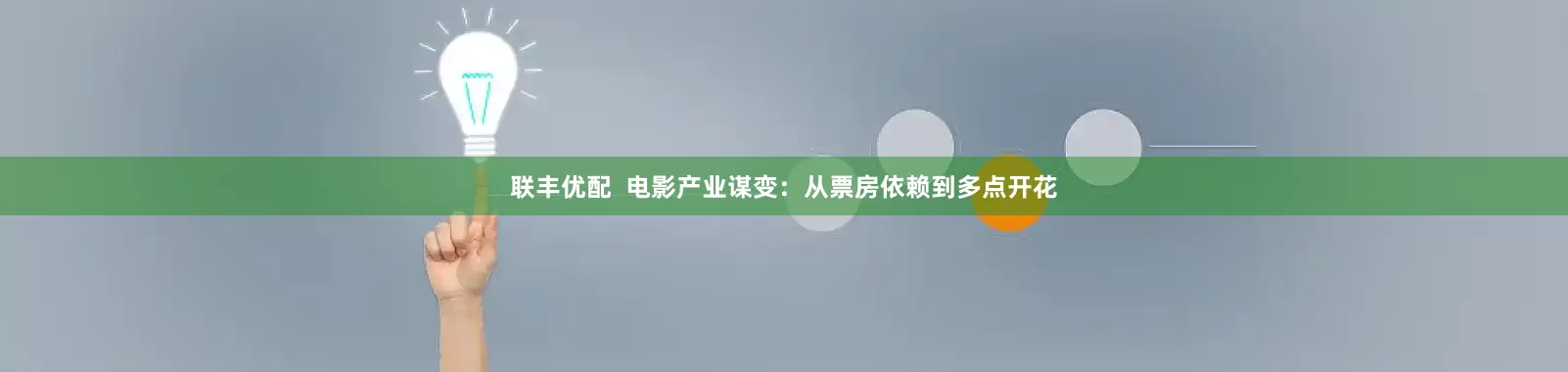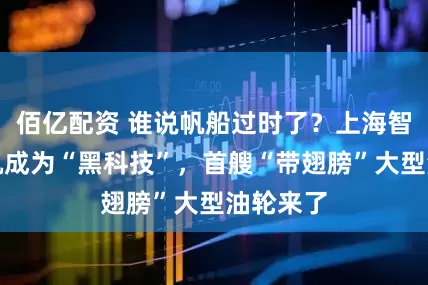老屋厨房的搪瓷碗柜里,那把铜汤勺正卧在青花瓷碗旁。勺身泛着温润的黄铜光泽易配资,是常年摩挲与汤水浸润的质感,勺柄末端缠着圈深褐的棉线,是外婆怕烫手特意缠的,勺底还留着几道浅淡的划痕,是早年熬粥时蹭到锅底的印记 —— 这是外婆嫁过来时带的嫁妆,算下来已有六十多年,它盛过清晨的小米粥、冬日的萝卜汤、年节的肉羹,把一家人的三餐四季、烟火温情,都悄悄盛进了铜勺的弧度里。
第一次跟着外婆用铜汤勺,是个初冬的清晨。天刚蒙蒙亮,灶膛里的柴火已经烧得旺,外婆站在灶台前,揭开冒着热气的铁锅,锅里的小米粥正咕嘟咕嘟冒泡,金黄的米粒在汤水中翻滚。“来,帮外婆把粥盛进碗里,” 她把铜汤勺递到我手里,勺柄的棉线带着灶间的暖意,“盛的时候慢着点,铜勺沉,别洒了。” 我握着勺柄,学着外婆的样子,把汤勺轻轻探进粥里,滚烫的粥水漫过勺身,铜勺瞬间变得温热,小心翼翼地把粥倒进粗瓷碗,米粒粘在勺壁上,外婆用筷子轻轻刮下来:“可别浪费,这都是好粮食。” 那天的小米粥,盛在碗里还冒着热气,我捧着碗小口喝着,粥里除了米香,仿佛还藏着铜汤勺特有的温润,暖得从舌尖一直热到心口。
铜汤勺的勺身与勺柄间易配资,藏着无数个家常的印记。勺底的划痕,是我小时候学熬粥弄的 —— 那时总爱跟着外婆在灶台前打转,趁她不注意,踮着脚拿起铜汤勺搅粥,力气没掌握好,勺底重重蹭在铁锅上,划出几道白痕,我吓得赶紧把勺放下,外婆却没怪我,只是笑着说 “以后小心点,铜勺经得起蹭,粥可经不起搅糊”;勺柄的棉线,换过好几回,最近一次是去年冬天,旧棉线被汤水浸得发硬,外婆戴着老花镜,用新的棉线一圈圈缠上去,还在末端打了个小结:“这样握着手不滑,也不烫。” 现在摸着那圈松软的棉线,还能感受到外婆缠线时指尖的温度;最特别的是勺身内侧的包浆,是六十多年来盛过的汤水慢慢浸润形成的,无论是清甜的蔬菜汤,还是浓郁的肉汤,都在铜勺上留下了痕迹,现在哪怕盛清水,勺身也泛着淡淡的暖黄,像把所有的烟火气都凝在了上面。
展开剩余60%它最 “忙碌” 的时候,是每年的除夕。从清晨开始,铜汤勺就没停过工:先是盛煮好的红枣莲子羹,给早起忙活的家人垫垫肚子;接着要熬制年饭必备的肉羹,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炖得软烂,用铜汤勺反复搅拌,让肉香与汤汁充分融合;到了傍晚,还要用它盛鱼丸汤,雪白的鱼丸在汤里浮浮沉沉,外婆用铜汤勺舀起一勺,吹凉了先喂给我:“尝尝鲜,今年的鱼丸做得筋道。” 全家人围坐在八仙桌旁,铜汤勺被放在餐桌中央的汤碗里,谁想添汤,就拿起它舀一勺,勺柄上的棉线被无数双手握过,带着每个人的体温。那天的铜汤勺,盛的不只是汤水,更是团圆的热闹,是一家人围坐的温馨,是刻在骨子里的年味儿。
铜汤勺也曾 “歇” 过,是在外婆生病那年。她的手开始有些颤抖,再也不能稳稳地握着铜汤勺盛汤,灶台前少了她的身影,铜汤勺被放进碗柜的最里面,勺身渐渐蒙了层薄灰。有次我试着用它熬粥,却总觉得不对味 —— 要么粥熬得太稀,要么盛的时候洒出来,看着手里的铜汤勺,忽然想起外婆握着它的模样,眼泪忍不住掉在勺身上易配资,顺着铜面滑进锅里。后来外婆身体好转,第一件事就是从碗柜里翻出铜汤勺,用软布擦了又擦,直到勺身重新泛出光泽:“灶台上没有铜汤勺,总觉得少了点什么,煮的汤都不香了。” 那天她坐在灶台旁,指挥我添柴、搅粥,自己则握着铜汤勺,慢慢盛起第一碗粥,虽然动作慢了些,却依旧熟练。
现在这把铜汤勺,依旧是老屋灶台上的 “主角”。每次回老屋,我都会帮外婆用它盛汤、熬粥,握着熟悉的勺柄,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踮脚学用勺的日子。女儿总爱凑到灶台前,仰着脑袋看我用铜汤勺盛汤:“外婆的勺子是金色的,好漂亮!” 外婆会把她抱起来,让她轻轻摸一摸勺身:“这是铜做的,比你的玩具勺子结实,能盛好多好多汤。” 女儿的小手放在温热的铜勺上,好奇地问:“它是不是陪外婆好多年啦?” 外婆笑着点头,眼里满是温柔:“是呀,它陪外婆走过了一辈子,以后还要陪你们走下去。”
暮色漫进厨房时,夕阳落在灶台上的铜汤勺上,黄铜的光泽泛着暖黄的光,勺柄的棉线在风里轻轻晃动。我握着铜汤勺,轻轻舀起一勺清水,看着水在勺里晃出柔和的弧度,忽然明白,这把外婆的铜汤勺,从来不是普通的厨具。它是岁月的 “容器”,盛着一家人的三餐四季,盛着外婆的疼爱与牵挂;它是记忆的 “钥匙”,只要一握住它,就能想起灶间的烟火、粥里的暖意、团圆的笑声;它是爱的 “传承”,把外婆的温柔、家常的味道,都藏在铜勺的每一道纹路里,等着一代代传递下去,永远不会冷却。
风从厨房的窗缝钻进来,吹动碗柜上的抹布,铜汤勺轻轻晃了晃,仿佛还在等着外婆揭开铁锅,等着盛起滚烫的汤水,等着继续把岁月里的温情与家常,一勺一勺,盛进每个人的心里,让那些藏在铜勺里的暖意,永远留在记忆的深处。
发布于:湖北省股海搏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